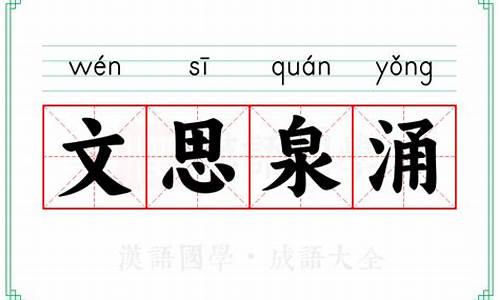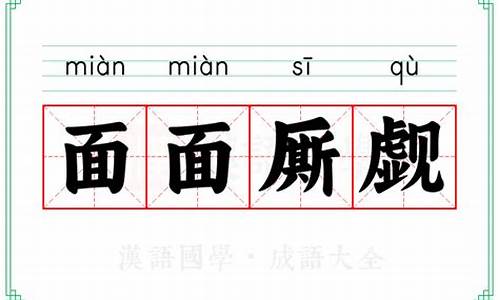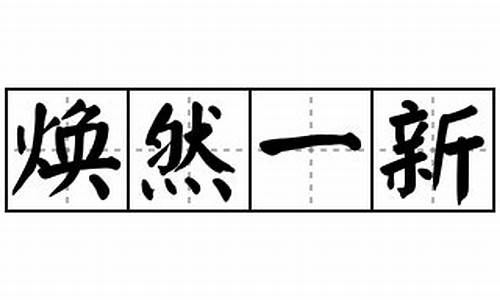零七八碎儿用普通话怎么说-零七八碎儿是四字词语吗
1.八笔顺笔画
2.老舍京味儿语言有什么特色?
3.张郎郎文学作品有哪些?
八笔顺笔画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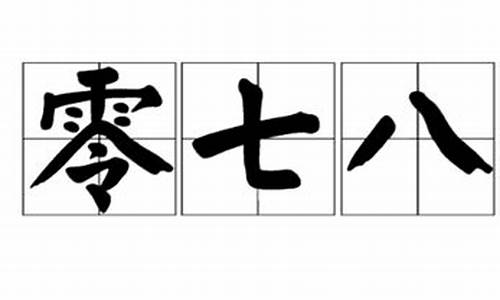
八的笔顺是:总笔画2笔,1、ノ(撇)、2、?(捺)。基本字义解释如下:
“八”,现代汉语规范一级字(常用字),普通话读音为bā,最早见于商朝甲骨文时代,在六书中属于象形字。“八”的基本含义为数名,七加一,如八面玲珑、八卦;引申含义为次第,即第八,如八年。
组词如下:
四面八方、四平八稳、四通八达、五花八门、乌七八糟、杂七杂八、八仙过海、七上八下、横七竖八、四平八稳、七零八落、零七八碎、正儿八经、半斤八两、八拜之交、七嘴八舌、乱七八糟、八哥、八角、王八、八方、腊八、八路、八成、八节、八端 、八戒。
造句如下:
报上尽是杂七杂八的广告。
他有了些钱,不过都杂七杂八地花掉了。
储藏室里放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很多,你说的那种零件不知放在哪儿。
几个星期以来,我一直忙着打发这间公寓里的东西,试图说服那些杂七杂八的物品散去,别来烦我。
你还得完成杂七杂八的事务。
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原因,不过她确实也在为家庭,成绩,还有学校杂七杂八的事情烦恼,总是很沮丧。
储藏室里放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很多。
老舍京味儿语言有什么特色?
老舍京味儿语言的特点是
1、语言的节律性强
老舍语言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,音节界限分明,并且语调的抑扬顿挫,有音乐性强的特点。吸取曲艺中的音律性,使作品更为传神有味儿。音节组合多为五字或七字,组合后因节律鲜明有律动感,加上声调的高低变化和语调的抑扬顿挫,使得语言朗朗上口。
2、多用儿化音
北京话里儿化音较为丰富,儿化是普通话的音变现象,儿化不是单纯的语音现象,它有区别词义,区分词性和表示细小、轻松或表示亲切喜爱的感彩。儿化音长期存在可以突出人物性格,语言风格,是烘托气氛的重要手段。
3、叹词、语气词和句调的运用
句调是指整句话的音高升降的格式,是语句音高运动的模式。句调在句末音节上表现特别明显,并且贯穿在整个句子中的。升调常用来表示反问、疑问、惊异、号召等语气。
4、小短句的运用
《茶馆》里面人物对话多使用小短句,没有过多的长句。长句更为文学性,多为抒情所用,而小短句急促,结构简单,表意灵活,简单明快,多用于描述迅捷的动作,或传达兴奋紧张激动的情感或者果断肯定的语气。
5、句式多用动词肯定和否定并列
老舍的北京话是经过凝练而成的文学语言,比日常的北京方言更为简练,利索,更富有表现力,京味儿更浓。这与北京方言中的句式有很大关系。
张郎郎文学作品有哪些?
张朗朗
文集
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出生于延安, 六八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。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,院刊编辑。之后曾任《国际新技术》杂志总经理, 《中国美术报》副董事长,香港《九十年代》专栏作家。出版文集《从故乡到天涯》和《大雅宝旧事》。现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, 同时在美国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。
? 一
? 一九七○年代, 我听说许多人在全国各地草棚里、油灯下, 一肚子理想, 满脑门子深刻。在写着、画着、唱着, 做着文艺梦。都是形形色色、不同层次、不同境遇的理想主义者。玩文学的差不多都是这种人。他们琢磨、创作, 试图活出个模样, 寻找意义。
? 也许他们就这样歪打正着, 一不留神为中国文学艺术传承做了很多事。
? 在那个年代, 大面儿上看来是个文化贫瘠的时光, 他们这些活动渐渐形成了文化潜流, 在地下交汇着、涌动着。所以, 到了八十年代才会有那样一次划时代的文化群体勃发。
? 我也许是由于喜欢写东西, 曾经组织过一个文学沙龙, 还在酒后茶余口无遮拦, 于是,在那个年代蹲进了监狱。也算是那个年代里间接对文化传承「有所贡献」。大概, 正如鲁迅老头儿说的: 咱萌不了芽, 还当不了供天才们生长的泥土吗?那些年头, 的确我当的就是最底层的泥土。
? 一九七○年代开始的那个午夜, 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, 是在油灯下守岁。不过, 大多数人在农村、在农场。而我却在牢房。平时屋里再冷, 今夜炉子一定要火旺。也许, 这意味着来年没准儿会转转运。我们这儿的炉子, 你一定没见过。这是当地名为
? 「扫地风」的全泥炉子。「扫地风」没有炉膛, 没有炉箅子, 没有任何其他炉子必备的金属附件。整个炉子都是用土坯砌成的。当地人凭多年经验,知道如何利用炉子内部特别的结构形成空间, 还有炉子底部有别样通风口。不用风箱, 自来就有风,所以得此名。「扫地风」是当地穷苦人专利。除夕那晚, 「扫地风」威风八面, 炉火通红。
? 那是在河北省饶阳县大狱里。
? 此前, 我从没到过这个地方。这是衡水专区的一个县, 这儿属于一个革命老区, 曾经是抗日最活跃的地区之一,老乡至今还记得吕正操、程子华这些当年在这里亮剑的英雄好汉。我们这群北京, 被下放到这里,这是当时副统帅一号命令所决定的。那时全国、全民都在准备打仗。
? 是得准备, 于是我们这些北京被准备成了饶阳。
? 当时我党应付局势的架势与心态和保卫延安时候一模一样。「要有准备」是多方面的。必然包括对脑瓜子里有问题的文化人进行必要准备。保卫延安时候, 给王实味准备一把斧子就行了。这会儿王实味们实在太多了, 全准备斧子也不行。
? 于是, 一批批我们这种人从北京被押送出来。这些脑瓜子里不对味儿的人中, 包括「大小刘麻子」英若诚和他太太吴世良, 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杨秉荪,歌唱家刘秉义、郑佐成、王芃等等。当然, 也包括我和老七这些无名鼠辈。把这些不安份和不可靠的家伙放在老根据地,有利于战时管理。这个地区有革命传统经验。
? 后来, 我听当地的一个老干部告诉我, 在打日本那会儿,他们晚上经常的任务是「掏窝子」, 就是清除异己的意思。半夜三更, 几个县大队的小年轻, 就去甚么人家把目标人物罩上眼睛、堵上嘴,拉出村。宣布他的罪行, 然后为了省子弹, 就手工处理了。有一次, 他们去某村去掏一个汉奸嫌疑, 没掏着, 就把他老婆掏出来了。为了打击汉奸,这老婆扔进枯井也能灭他们的威风。在扔下枯井之前, 小年轻们都上下其手「摸摸」。小王是近视眼, 也抢着去摸。别的队员笑了, 说: 「瞎子,看清楚喽, 那是你姑啊! 」那些村的人, 很多都有亲戚关系。小王说: 我不管, 我摸的是汉奸婆! 众人齐声喝止: 我们都行, 就你不行,汉奸归汉奸, 也不能乱了辈份。
? 听到这儿, 我明白了。人家这儿管我们这类人有经验着呢。
? 我前面说这是县大狱, 其实是传统习惯说法。确切地说, 我们由于还是未决犯, 所以关的地方还不是监狱, 而是公安局下属的看守所。
? 这县公安局看守所老所长, 也姓张。他还是老区传统做派: 不穿官衣。就爱穿着对襟黑棉袄, 一条絻裆裤, 手里提着个抗战时期的镜面盒子炮, 和当年闹日本那会儿的捯饬还一个模样。估计那是他一生中最闪光的年头儿, 那年代绝不能忘。
? 饶阳这地方到处都是盐硷地, 还非常缺水, 真是「咬在瓜把儿上了—— 苦得厉害」。周边的几个县, 从来都不怎么富裕。有些县农忙一完,就整村整村出去「混穷」, 去讨饭, 把自家的粮食省下来。饶阳县的人, 很要面子, 丢不起那人。他们也到全国各地去「混穷」, 可绝不要饭,他们耍的是本乡绝门手艺—— 劁猪。就拿着一个劁猪刀子, 走遍全国, 吃万家饭, 和古代侠客有几分神似。
? 除夕之夜, 这个穷乡僻壤老乡们噼里啪啦放了不少炮仗, 好像这儿炮仗不要钱似的。原来, 这块大盐硷地产硝。所以「搓炮仗」就成了这儿的重要副业之一。今儿晚上人们放的炮仗都是自己生产的, 才能可劲儿地造。
? 我们这伙人, 是一九六九年底从北京公安局看守所(就是那着名的K字楼和王八楼) 押解到这儿来的。其实不过才三个月左右, 已经把我们给彻底饿废了。
? 现象是, 这伙人里连大小伙子们都不会跑马了, 的确也没马可跑了。甚至连生病都不会发烧了。人们开玩笑说, 咱们都成人干儿了, 细菌也全饿了。
? 人们坐在炕上闲聊, 有人发现我们这些人(甚至包括我们中间最胖的李友钿先生在内) 紧并着的两条大腿之间都出现了一个横拳那么宽的空隙。大腿上的脂肪理所当然地消耗殆尽。
? 北京公安局规定看守所里一人一天八两粮食。每个窝头二两, 正好四个窝头, 一天两顿。在北京, 人们已经觉得饿得前心贴后心。据说,当年批这个定量指标的人, 是北京公安局长冯基平先生。中, 他也被关到这儿来了。人们传说, 他为此后悔不已。谁会想到,八两粮食怎么这么不禁吃啊?
? 每天除了这窝头之外, 就一碗菜汤。甚么菜便宜,就是甚么汤。偶尔有点儿肉末儿, 那就属于上上佳肴了。当然, 逢年过节如果「形势大好」, 我们还会有点儿改善。那阵子,我们已经被改造成了这种人—— 天天想的就是一个「吃」字。除了睡觉时间以外, 肚子全天候都在和你较劲。
? 到了饶阳, 每天倒是三顿, 定量也是八两。早晚各喝二两粥, 中午有两个号称二两的「饼子」。就连当地的农民进来以后, 第一次开饭的时候惊讶得眼睛都直了, 绝没想到伙食这么凄凉。有人当场就掉泪, 也有人用脑袋去撞墙, 刚进来的人, 胃酸都劲儿大。
? 我们喝的稀饭可以当镜子照, 身体也都和那粥差不多, 饿得快透明了。可是当地人, 比我们招儿多, 他们很快就找到「抗饥」的窍门, 那就是,越饿越得有存粮, 中午那两个高粱麪的饼子, 最多吃一个。一定得咬牙留下来一个, 到后半夜饿得无法睡眠的时候, 一点儿一点儿,慢慢品。那就可以减弱胃酸对你的折磨。为了防止自杀, 每晚牢房里的都得轮流值班, 每个人两个小时。房上值班的解放军也是每两小时一班,他们在房顶上踱来踱去, 随时都可能点名。
? 这个县城, 竟然没有起脊的大瓦房, 一码儿的平顶**土房。机关或有钱人家才是砖房。我们监狱因为重要, 是砖房, 但也还是平顶房。房顶可以当场院用, 可以晒粮食, 还可以放哨。
? 这样的款式让值班解放军看守方便, 来回踱步。他们在房上叫到几号, 那个号值班的就立刻站到门前大声喊道: 「二号五个, 一切正常。某某某值班。」
? 你想想, 这时候要不是有存粮钉着, 你怎么熬过那漫长黑夜里的两小时? 我们这屋「扫地风」比别的屋子也大一号,给的煤饺子也比别的屋子多一倍。这儿的煤球不是用筛子摇出来的, 所以不是圆的, 这儿是把煤末子和黄土和成了煤泥之后,就用我们的饭碗当工具做煤饺子, 擓出一个个月牙形的煤泥, 往地下一磕, 就齐活了。一开始, 这活儿都把我们这伙人看呆了,那煤泥绝对是煤少土多, 那颜色一点儿都不黑, 快和新四军的军装颜色差不离, 灰不拉唧的。我们想, 这成色的煤饺子, 有法儿着吗? 没想到,这儿的煤还挺好烧, 就这种灰色煤球着得旺着呢。
? 为了节约, 我们屋一个星期才分给一百个煤饺子,平均每天只能烧十四个, 而其他小号每天只能烧七个。二十四小时都烧, 绝对不够。所以一到傍晚我们就必须封炉子, 一直封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,才打开火。封火的时候, 把半块煤饺子研成细粉再用水和成煤泥, 糊上炉口以后, 再用一根磨细了的筷子扎一个隐约可见的小洞。从那洞口,隐约见到煤火的红色这样才能耗到第二天。
? 所以, 每夜下来, 我们碗里的剩水都结了冰, 被口嘴边那儿, 都有一块由我们整晚哈气形成的白霜。每个值夜班的, 都冻得只能坐在炉台上。所以, 每个棉袄的背后都有一绺如屋漏痕般的焦黄—— 那是封火后的微小火眼升腾出来的热气所为。
? 那时候, 我和拉小提琴的杨秉荪正好在一个房间。我们那个房间是个把角儿的大屋子, 住了十来个人。别的小号才有五六个人。我们屋连炕都没有,在地上铺了些麦秸算是我们的铺位。所长对我们说: 这些麦秸在这里也是「稀罕物」, 麦秸比稻草隔寒隔潮, 是打地铺的上好材料。
? 话是这么说, 对我这个风湿性心脏病患者来说, 这地铺再「高级」, 在这不见阳光房间里地气阴潮, 照样让我忐忑不安。
? 当然, 这儿也有这儿的好处。北京倒是住楼, 还有电灯, 还有够份量的窝头, 还干燥爽朗。但那儿管的太严了, 每天除了改造自己, 就是批斗别人,其余时间都得坐在那儿学习, 还得坐得笔管条直。你连找个人聊个天, 都得和地下工作者那样机警, 才能偶尔进行。
? 这里物质条件差多了, 可是根本没人搭理你。你爱看书就看书, 爱聊天就聊天, 爱干嘛就干嘛, 只要你别打架闹事, 他们只要求你老实呆着就行了。
? 人生何处不相逢, 杨秉荪万万没想到, 在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」—— 饶阳县, 见到了上一次在莫斯科见到过的老朋友李友钿。你想想那年头儿,有几个人出过国? 老杨人家是苏联、匈牙利双料留学生, 在那儿学的是小提琴。老杨和我属于一个大案子进来的, 都是因为传说了文化旗手的笑话。
? 老李从来不说政治笑话。他本来是上海的一位名厨, 阴错阳差被外交部选中, 派往国外常驻, 在莫斯科和布达佩斯都呆过。在中,有人在国外揭发他买菜中间可能有猫腻, 北京外交部造反派就勒令把他押解回京。他一听脸就白了, 那个火红年代押解回去,肯定凶多吉少。天生慈眉善眼温顺的他, 半夜就逃出使馆, 企图「叛国投敌」, 结果, 还是被抓了回来。
? 当年, 老杨是使馆请来的艺术家, 给国际政要献艺。老李则负责演出后给大家准备上好的佳肴。你想想, 那时候他们是甚么架势, 甚么派头? 吃甚么? 喝甚么?
? 在饶阳这里, 他们大眼瞪小眼, 喝着白开水, 等着下顿的黑李逵饼子。这儿的饼子刚下锅的时候是黑红黑红的, 近似巧克力颜色,等凉了下来就黑得像铁疙瘩一样。这是全高粱麪的饼子, 所谓全面就是在磨麪的时候, 把能磨的东西都磨进去。不出麸子不出糠。这样的粮食实惠,所以才那么黑。
? 老杨和几个同屋的人, 每个人都拿着各式各样的本子, 各种各样的笔, 一本正经围坐在老李的周围。老李用他无锡口音普通话给大家讲解一道道名菜的做法。
? 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。固然, 越写越饿, 越饿越写。别看老李已经饿成细脖大脑壳了, 可讲起来菜谱, 还是当年着名大厨的谱儿, 言简意赅,形容准确, 细细道来, 不紧不慢。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, 他口中的每一道菜都精致无比。无论中餐还是西餐都可以录入最顶级的菜谱。就这样,我国的饮食文化得到了一次成功的传承。
? 我这人虽然也喜欢吃好的, 但绝不是一个美食家,所以向来对饮食文化就兴趣不大, 这会儿又饿得要命, 他们还一本正经坐在那儿进行精神会餐, 那胃脏一定更加难受。所以, 我不去听。老杨说:不会, 精神会餐可以分散注意力, 就减轻胃脏的痛苦。再说, 你学好了这些手艺, 出去以后一定大显身手, 自己彻底伺候自己一把。
? 当时我们屋子里大概有十二、三个人, 七、八个人都参加了那个精神宴会。
? 我呢, 正给几个小年轻侃故事。当我侃完一个故事, 他们正七嘴八舌争辩的时候, 一位叫段铎的小伙儿突然说: 「你别就光给我们穷侃了, 干脆教教我们, 也玩玩文学、写写诗。」
? 段铎那时候大概还不到二十岁, 饿瘦了更显年轻。原来, 他发现我在牢房里靠侃故事就可以占据一席之地。在这儿, 这也算一种本事, 要练别的本事, 这里边儿没条件。要练文学, 就是练嘴、练笔, 在饶阳绝对有这条件。不练白不练。
? 他话这么一说, 其他几个年轻人都同声附和, 齐齐嚷嚷要拜我为师。段铎学习的根底很好, 因为出身问题, 没被大学录取,只好上了一个中专。虽然他一直喜欢文学, 可没机会玩文学。另一个同号叫王涛, 是青龙桥的一个着名玩主, 那片儿住的都是正儿巴经的八旗子弟。于是,他们就开始听我侃诗。
? 年底之前监狱进行调号, 把老杨和老李他们都调走了。
? 我和这些北京来的小伙子们还留在这个大号里, 就开始一起写诗、评诗。段铎是个非常聪明的青年, 他本来是在中专学电机的。我先教他背一些新诗、旧诗, 让他体会诗的意境是甚么, 优美在甚么地方, 如何在文字里寄托笔者的情愫。
? 从苏东坡的《水调歌头.大江东去》到柳永的《雨霖铃》, 从普希金的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到艾吕雅的《你好, 哀愁》等等, 我给他瞎背一气, 他就瞎记一堆。
? 别人聊天的时候, 他就在那里瞎背。为了记得清楚, 他就把刚趸来的货都抖搂给王涛。不用几个月, 他和王涛, 还有景山东街的小亓都背了不少从我这里趸去的二手诗作。
? 后来, 以小段为首的这伙孩子, 一人钉了一个本子用来抄诗。后来, 把我搜肠挖肚的所有零七八碎都背完了, 就只好一起命题自己来写诗,每个人都写。他们各有千秋, 全都进步神速。你想想那个王涛, 本来是个玩主, 现在居然和我们一起写诗。小亓喜欢写古诗,写完后也和我们切磋一番。小段两样都试试, 虽然他是浅尝辄止, 写的诗味还是很浓的, 对一个学理工的孩子来说, 就很不容易了。
? 除夕那一夜, 我们都没睡觉。除了留下来中午的一个饼子以外, 我们还把晚饭稀饭里的胡萝卜,也留了下来当年夜饭。我们把胡萝卜围放在「扫地风」的火口边, 真都烤成了透明的胡萝卜。吃起来有点咬劲儿, 还香甜无比。后来,看到莫言的小说里描写的透明胡萝卜, 似曾相识。那天晚上, 我们约定在一小时内各自写一首诗。
? 王涛写了一首自由体的新诗, 题目就叫我们大为惊叹—— 《我是流氓! 》他生动热情地标榜自己就是一个流氓, 谈到流氓的快乐, 流氓的自由,流氓的流浪, 流氓的超越。我们纷纷叫好, 每个人还都和了一首—— 《可惜我不是个流氓! 》、《我心里就是个流氓! 》、《我也想当个真正的流氓!》
? 我们轮流朗诵, 笑得满地打滚。那时我们非常快乐。我们把这几首诗钉在一起,封面上我用美术字写上《流浪者之歌—— 一群快乐的流氓》。我看大家越来越上瘾了, 写作热情高涨, 就说: 干脆咱们办个报纸,当年在渣滓洞人家陈然还办了个《挺进报》, 咱们也在这里办个解闷儿的文艺报, 怎么样?
? 他们三个齐齐喝彩, 我就开始主办这个报纸了。其实, 每次只是一张大纸, 那是我们用粥把几张纸粘在一起。这张报纸只有正反两面,一共两版。我本来就是学美术的, 所以我先画好了版样, 他们的稿子,也都由他们自己抄写在预留给他们的版面上。我还给每首诗都画了插图。用了两个下午, 我们第一期就出版了。
? 当然, 我们很小心。每次出版以后, 大家悄悄传阅。当然, 只是在我们这几个人中间, 多一个人看了,我们被发现的机会就多了不止一倍。不是特别近的朋友, 决不传阅。我们本来商定, 看完就毁掉, 可是, 每次大家还是舍不得,于是就分别保存着。我们说好了, 谁的万一被发现了, 就说是自己写着玩的, 别人就尽快销毁。
? 阴历大年初二, 又调号了。这次我分到一个只住五个人的小号, 和杨秉荪分在一个房间, 我很高兴。就在半夜他值班的时候,我悄悄地把我保存的那份报给他看了, 他看了非常快乐, 拼命忍住笑声。不过, 他抹抹眼睛, 叹口气, 说: 「别舍不得,快点儿销毁了吧。这地方, 这件事就可以算是重新犯罪。安全第一呀。」
? 我知道他说得对,我就是为这种罪折进来的。于是, 立刻把它塞进了火炉, 眨眼间, 这张报纸就化为一缕青烟。这也是在县大狱的好处, 这里没有暖气。冬天只好生炉子,要是在北京看守所要销毁点儿甚么就没这么容易了。这里销毁一篇文章之类的东西实在太方便了, 原始环境有原始环境的好处。
? 二
? 我本来想过两天找个机会告诉他们仨, 都销毁了才保险。可计划不如变化。
? 大年初四(一九七○年二月九日), 监狱里人们前两天遇上了难得的改善, 肚子里终于有了点儿宝贵油水。混了个肚儿圆, 大家心情就爽朗了起来。
? 刚喝完早饭的粥, 张所长就提了镜面盒子炮上了房, 解放军也在房上架起了机枪。这里的们, 非但不会为此而紧张—— 对他们来说这早就是家常便饭了—— 反而都兴奋起来。人们嘀嘀咕咕: 「有戏! 今儿肯定有戏! 」哪出戏并不重要, 有戏就有得看。
? 老张头看各路人马都布置齐了, 在房上开始发话: 「田寿鹏, 出来! 打开库房, 叫到名字的人自己把行李搬出来, 再到库房把自93 己东西都拿出来, 在当院打好铺盖卷, 然后都就地咕嘚着等叫名字。叫谁谁出来。」人们都兴奋无比, 人挪活、树挪。再不挪,我们耳朵后头该长青苔了。
? 「索家麟, 王涛, 宋惠民, 朱章涛, 田树云, 张郎郎... 」老张头儿这么挨个点名, 接着他还点了我的同案老七等等。我同屋的其他人都对我拍拍打打, 表示祝贺, 说: 好啊, 你小子发了,别忘了我们哥儿几个。我一边收拾东西, 一边说: 「发甚么发? 纯粹是骑驴啃烧鸡—— 这把骨头指不定扔哪儿呢! 」人们纷纷说: 挪就好, 挪就好
声明: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,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,均为采集网络资源。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,可联系本站删除。